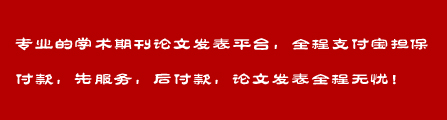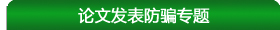毕业论文发表,《新诗》社中杂记
日期:2010年05月23日 来源:原创 热度:
在一些学校,各个专业执行的情况不同。这个是学位条例规定要这么做的,教育部规定先要写学年论文发表,逐步逐步积累经验以后,在毕业的时候撰写毕业论文发表就不会成为一件太难的事了。但是有很多学校没有把学年论文当作是一个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途径或者是工具。..
学年论文发表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在一些学校,各个专业执行的情况不同。这个是学位条例规定要这么做的,教育部规定先要写学年论文发表,逐步逐步积累经验以后,在毕业的时候撰写毕业论文发表就不会成为一件太难的事了。但是有很多学校没有把学年论文当作是一个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途径或者是工具。那么,临近毕业的时候,学生还不知道毕业论文发表该怎么写。当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院校是很注重学年论文的撰写的,因为只有训练学年论文的写作才能顺理成章的过渡到毕业论文的写作。每一门课的授课到最后的考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在训练一学期或一学年论文的写作。因为任课老师都是从自己的课程的角度出发给大家考一点知识题,再考一个论述题。那么对于论述题,应该说有经验的老师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论述题来训练学生写论文的。有一部分学校这样做了,但还有部分学校没有将其提到日程上来。还是由各个老师具体要求,让学生当一次作业来做的,没有强调学术性。
《新诗》社中杂记
▲第一,我们应该感谢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这五位先生对于本刊的赞助和合作,把编委这重大的任务担负下来。我们也应该感谢各位诗人诗论家的寄稿,使本刊添了不少光彩。如果没有这些对于新诗的热忱的拥护者的通力合作,本刊是难以产生,难以长成并也难以对于中国的新诗坛有一点赏献的。
▲本刊的内容大约分为作诗,译诗,释诗,诗人诗派之研究介绍,关于诗学之一般论文,诗坛人物访问记回忆录,诗人书札日记,诗书志,新诗闲话,国外诗坛通讯,诗歌问题之讨论,以及诗人肖象手迹与诗书插绘等栏在这一期上,我们虽然不能每栏都有,但这个遗憾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总可以补偿的。
▲本刊创作诗歌刊登的前后,均以作者姓氏笔划之繁简为序,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最适当的排列法。创作诗歌每期所占的篇幅大约是四十页至五十页光景,即每期篇幅十分之四至十分之五,统用新四号字排印,以醒眉目,并以表示本刊对于创作诗之重视。用这种字型排印,在杂志界上可称是一个创例。
▲对于外国诗人的介绍,以当代诗人或给与当代诗人大影响的前代诗人为主。在介绍一位外国诗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同时刊登出关于这位诗人的研究论文等,并附以与所介绍诗人有关的插图,使读者能够有一种比较有系统的认识。这种介绍是以外国诗人本身为本位的,所以以译者的艺术见长的零碎的释诗,我们拟暂时不登战。
▲正如读者所能见到的,本刊并不是某一诗泪的专志或某一新诗运动的代言机关;本刊所企望的,只是使这枯萎的中国诗坛繁荣起来而已。所以,不论以怎样的形式写,凡是有独创性的好诗,本刊是无不乐与刊登的。
▲本期原有朱光潜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论文两篇:朱先生的“两积心理典型和两种诗”和金先生的“论胡适之体”。因为已失去时效,并依了作者自己的意志;我们没有将他们刊出。朱光潜先生已答应我们另写论文一篇,在下期可以刊出。
▲本期中未能刊出的,尚有孙大雨梁宗岱两先生所译的“勃莱克诗抄”和周煦良先生所译的爱略特的“勃莱克论”,均移入下期。
▲因为本刊发排时期较早的原故,在排印时期寄到的诸名家的诗,均未能编入,这是我们应得向诸作者和读者道歉的。
(选自1936年10月10日《新诗》月刊第1期)
《文学》(新诗专号)编后记
本期特约撰译的论文,诗歌,与投稿,收到的件数超出我们的预计之外,照每年一月特大号的页数容不下。初时想续出一个专号,因为对多数的读者未免觉得单调,所以决计增加到三百页,就这样,还有几篇较长的译诗与论文,终于排不进去,临时抽下;如《苏俄的诗歌》,(高寒译),雨果与惠特曼的几篇长诗,只好在下几期中陆续刊载。这实在是不得已的情形,惠稿诸位当能鉴谅。
本期中的文字大概可分五类:(一)总论(二)批平(三)译诗(四)诗的创作(五)新诗写法,与其前途的自由讨论。还有不能归入这五类中的,如诗人的略传与英美现代的诗歌等。
为避免读者感到材料的单调起见,所以间隔刊登,译诗,诗创作,论文等不完全以类为限,不过刊载的先后绝无轻重于其间。
只是这一本的专号,要对中国新诗的批评方面十分完全,自然是难办到的。本期中有:茅盾先生《论初期白话诗》,有穆木天先生论《郭沫若的诗歌》,石灵先生论《新月诗派》,三篇都有精细分析的论断。虽然从前对于诗歌的评论不是没有,像这样的文字——无论批评一个时期,一个诗人,或一个诗派的评文也还少见。读者阅此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途径,自有概括的观念。(还有几篇专论一本诗集的批评文字,都移在二月号中发表。)
可以归入第一类的:朱佩弦先生的一篇《新诗杂话》虽然简短而语多扼要,公平。以他主持《新文学大系》新诗选的眼光来总论过去与现在的诗派,简明,切要,很值得重视。
如以《新诗的足迹与其出路》与《新月诗派》两篇对比看去,当然有些意见不尽相同;再则茅盾先生读美初期白话诗的形式自由,意象清新,而《新月诗派》的作者,则认为当时的自由诗,不过是造成新诗桥梁的一把泥土。这观点显见是多少差别,也许读者因此诧异,为甚么一本专号中有不很一致的议论,但编者却认为这正可给读者更深思,更从尔方得到比较的一种提示。我们早声明过了希望集合全国诗人与批评者的主张:评论,给新诗的未来共同开创出光明的前途,原不预备仅从狭隘的观点上去衡量所有的新诗作品。(但我们也自有我们的观点,非毫无限制,不过不太狭阴罢了。)而且每位评论者的见解,无论如何不能完全一致,却不是离奇,偏倾,或向朦胧隐晦中发议论;但就表达的方法,与对人生的看法上有些差别。或主张以毫无拘束的诗笔实现人生;或以节奏与文字的技巧,论一派的作者。那末,所见纵不尽,同并刊于一本杂志中,反使读者对中国新诗应走那条路有深切的了解,而对过去的作品也可以有种种的看法。
此外如在本期中特避《自由论坛》一栏,容纳征文中A,B,C,项的投稿,(以收到的先后为序)这栏中真有许多意见相反的理论,编者所以用这《自由论坛》四字,表示投稿诸君对新诗写法与前途的希望的不同处,读者自易明了。特为增多若干页的地位,发表各位的“我见”。——自然不是凡投来的一律刊登,除去所见过于单纯,文字过于幼稚者外,但在一方面能言之有物的,便给大家一个表示主张的机会。这十七篇文字,都对新诗有诚恳的态度与热切的希望,虽然是彼此不同,但读者历览各样的说法或感到多方面的兴味?至于如何说法,那是投稿者的“我见”,读者自会有判断的。
郭沫若先生的诗才与译诗的本领,早为大家所公认自译《浮士德》后,他久已没作长篇诗歌的翻译了。这次特为本刊将歌德的长篇诗剧《赫曼与宝绿苔》译出。这是一篇描写爱情的佳剧,人物的生动与德国当时乡村中的情形,经歌德作成,富有写实的成分,与《浮十德》的写法不同。以郭先生的委婉译笔译出可称“双壁”。但原诗过长,在本期中不能完全刊登,编者殊觉歉仄!希望读者注意二月号中的续译文。
其他译诗者如冯至穆木天高寒彭慧诸位对于原作素有研究,故皆有可读之价值。
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作品介绍到中文来的极少,李微先生由日文转译过来;在这国难严重,民族存亡的时代中,大家读到这位热情喷薄浴血战场的爱国诗人的壮作,尤当兴国。译为日文的是匈牙利Shiritori Kurakichi博士;他在东京作教授,精通日语,所以虽是转译,却不失原作的风度。
《中国诗中四声的分析》是朱光潜先生精密研究中国诗中选音用字的结果,以心理学,美作基点,比类分析,又与西洋诗互相证明,是极有价值的一篇论文。
至于刊登诗的创作,这是最繁难的事,但编者确改说是费过了很大的苦心。五十天的征稿期间,收到了约近三百份的诗歌创作。(大都是在十一月中寄出的)以时期追促,编者有七八天专作检选的工作,每份稿件无不予以深切的注意,绝不是只看一次便决定用否。虽然所刊登的未必尽如人意,(有甚么更好的方法能尽如人意呢?)编者自信就自己所能为力的对得起作者与读者。诗选中尽有新人,却也有出色的作品。
关于图书,中国故去的新诗人遗像,笔迹等,以前也散见于各种刊物上,但为纪念见,所以有的不避重复,仍然制版付印。如徐志摩先生未发表过的短诗稿,刘大白先生刘梦华先生的书信,都不易搜求。朱大柟君是当年在北平的一位最年青的诗人,虽没留下许多作品,他的诗确有他自己的风格;如果不是早死,当有更大的成就。
编者认为缺憾的是经过通信与向朋友中寻求,竟没找到诗人方玮德的照片!
今年正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百年忌,有几种刊物,如《译文》等已经介绍了他的一些作品。本期有耿济之先生译的《石客》诗歌剧一篇。以时间关系,以后只可陆续刊载他的著作,或介绍的论文。任本期中有精制的一幅三色版印普希金的油画像,与其亲笔画及《石客》插图等,都是可纪念这伟大诗人的珍品。
恰好在编者行箧中,有一本德国精印的歌德纪念画册,是去年带回来的。内有当时德国画家所作《赫曼与宝绿苔》白描画二幅,人物生动很见精采(这本画册共有一百九十二页,现已绝版,即在德国已不易购求了)。又有哥德的签名字迹,故制版印在译诗前面。
本刊初拟编一新诗详目,以备读者参考。适收到曲韩两位的来件,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册编目》,虽罗列颇广。但辑者似有未见之作,且目中所载亦有新人作的旧诗集。本刊乃先讬柳倩君添补,改正,加入若干种为原目所未有者。然因限于见闻,遗漏,差错在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此外还收到童养年君寄来一份《新诗集目录》与曲韩二君的相似,虽未采用,而寄者的盛意我们却一样致谢!
发刊这专号的微意,在献辞中已经说过,编者不再说甚么了。但诗歌是文学的原始,而激扬情国比文学中其他部门也最为有力。我们现在需要力的文字作品——需要慷慨激越的情绪的引动;更需要表现疾苦振作精神的诗歌。自然,我们不能忽视了诗的艺术,可不能再看艺术的外形而不问诗的内涵。在个人高兴写写,怎么样的诗都可写,有他的自由但对多数的读者,对水深火热的人生,为甚么我们只图个人精神的“羽化”,而漠视当前的苦难?假使杜甫,雨果,陆游,拜仑生于现代的中国,试想当有何等有力的作品出现。编者一点微意,再在这里加一番申述,近于重复,还望读者谅解。
编者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专作编辑这个专号的工作,风雪凄然,一灯相对,往往校阅,编排至深夜方眠;就连助理者也是终日无暇,但这样辛劳是负编辑责者应分承受的,如果读者认为这本“专号”还有他的一点精采,那便是编者的慰。
又是一度的新年,待到再过十二个月的光阴,看看我们的文坛,有甚么更进步的发展?
忠于所事,忠于所能,忠于我们自己的笔,与笔下的人生。
我们互相激励罢!在这山河破碎,“风饕雪虐”的时期中。
我们互相激励罢!广多的作者与读者:
让我们的笔,开出血热的心花!
让我们的手,握成坚实的环链!
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在上海的爆竹声中写完。
本文首发论文邦:http://www.lunwenbang.com
上一篇:教育论文发表,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时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
下一篇:职称论文发表,情系穷人,执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