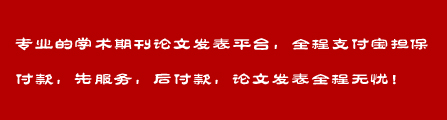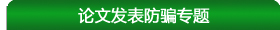编辑人的初衷
日期:2010年06月25日 来源:原创 热度:
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发表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发表,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发表。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这本诗集才得以呈献到今天的读者面前。 按照编辑人的初衷,年轻的..
学术论文发表的类别
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发表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发表,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发表。
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这本诗集才得以呈献到今天的读者面前。
按照编辑人的初衷,年轻的一代更是这本诗集所属望的对象,尽管里面作者们的名字一个个对于他们都很陌生。在文学史上,作品的生命从来并不取决于作者的名望;任何文学作品一旦问世,都将凭借自身的质量和价值,来接受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检验。本集的作者们将怀着感激的心情,不揣自己在文学史上几近湮灭的存在,期待年轻的月旦家们的评隲。
这二十位作者除个别情况外,大都是在四十年代初开始写作的,或者说是同四十年代的抗战文艺一同成长起来的。那时期,民族危机笼罩着整个神州,蒋介石、汪精卫们出卖着祖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肩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给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历史上,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是反动的年代,也是进步的年代;是黑暗的岁月,也是光明的岁月;是悲惨的绝望的时刻,也是战斗的充满希望的时刻。这些作者是在这样尖锐的矛盾环境中提笔写诗的,严酷的政治形势不能不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当时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没有也不可能经受正式的专门的文学陶冶,现实生活才是他们的创作的唯一源泉。四十年代的现实生活空前动荡而又空前广阔,他们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国统区,有的在前线,有的在后方,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城市,有的在公开的战斗行列中,有的在秘密的艰苦的地下。不论他们的处境如何相异,他们都生活在中国的苦难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炽烈的斗争中。他们在政治上有共同的信仰和向往,坚信并热望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普通人民的一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和先进人民相结合的程度可能是有限的,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却恳切面热烈,并带有鲜明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以及体现这种倾向性的艺术手段,可以由他们的作品本身来作证。
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二十位作者也不例外,他们在艺术上都只能是他们自己。但不妨指出,他们尽管风格各异,在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却又有基本的一致性。那就是,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以及因此而来的对于中国自由诗传统的肯定和继承。中国的自由诗从“五四”发源,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到三十年代才由诗人艾青等人开拓成为一条壮阔的河流。把诗从沉寂的书斋里、从肃穆的讲坛上呼唤出来,让它在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中接受磨练,用朴素、自然、明朗的真诚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这便是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本集的作者们作为这个传统的自觉的追随者,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不过,接受影响决不等于模仿和因袭;相反,他们从艾青学到的,毋宁说是诗的独创性。没有独创性,就没有诗,也就没有人和他的战斗。因此,他们尽管成绩菲薄,却努力争取走出自己的路。然而,企望在诗艺上真正有所建树,把自由诗传统向前推进一步,那又谈何容易?充其量只能说,他们各自进行了诚实而艰苦的探索,并由于气质和风格相近,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吸引、相互感染、相互激励前进的流派,这倒是他们始料所未及的。而且,即使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它也不能由这二十位作者来代表;事实上,还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诗人,虽然出于非艺术的原因,不便也不必被邀请到这本诗集里来,他们当年的作品却更能代表这个流派早期的风貌。单就这二十位作者而论,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和成就也各不相同:有些当时已经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有些当时还只是一个“初来者”。但是,作为一个流派,这些作者都分别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它作出了呈献。此外,如众所周知,胡风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对于诗的敏感和卓识,以及他作为刊物(《七月》,《希望》)编者所表现的热忱和组织能力,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壮大起过了不容抹煞的诱导作用,这一点也是可以由四十年代的文学史料来作证的。
既然只是一个流派,本集作者们在潺潺汇聚并向前探索的同时,不能不承认其它流派的存在。事实上,在四十年代,由于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推动,中国的整个诗歌运动是非常蓬勃的,各个流派的诗人们都为祖国人民的抗敌救亡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解放区,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诗歌运动更取得了崭新的丰硕的成果。本集作者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一点精神劳动所得,同人民诗歌的海洋相比不过是微微的涓滴。今天,他们在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鼓舞下,请求读者对他们重新加以检验,正是诚恳地抱着“涓滴归海”的希望。
既然作为一个流派,他们对于诗的本质又自有他们的共同理解。他们究竟怎样来理解诗呢?
与其说“诗必须是诗”,还不如说“诗决不是非诗”。首先,他们认为,诗的生命不是格律、词藻、行数之类所可赋予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诗在写出来之前就蕴藏在客观世界,在什么地方期待、吸引和诱发着诗人去寻找,去捕捉,去把握。诗又不是现成的,不是可以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的;它执拗地在诗人眼前躲闪着,拒绝吹嘘“倚马千言”的神话,尤其抗拒虚假的热情和侥幸的心理,要求诗人去发掘,去淘汰,去酝酿,去进行呕心沥血的劳动。然而,诗的主人公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跃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不论字面有没有“我”字,任何真正的诗都不能向读者隐瞒诗人自己,不能排斥诗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排斥了主观抒情,也就排斥了诗,因此诗中有希望,有欢快,有喜悦,也有憎恨,有悲哀,有愤怒,却决没有冷淡的描绘或枯燥的议论。
其次,他们认为,自由诗的形式并非如它的反对者们所设想,没有规律可循,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恰巧相反,诗人十分重视形式,正因为他重视内容,重视诗的本身。形式永远是活的内容的形象反映,必须为内容所约制,不可能脱离对内容进行发掘、淘汰、酝酿的创作过程而先验地存在。因此,诗的形式应当是随着内容一齐成热,一齐产生的;如果把后者比作灵魂,形式便是诗的肉体,而不是可以随便穿着的服装。因此,诗的形式就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而是和内容不可分割地成为整个诗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内容创造形式,有时也会破坏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有时也会窒息内容。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才是诗的极致。
诗的客观性和诗人的主观性之间,诗的内容和诗的形式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这几点,本集作者们和不同流派的诗人们应当没有什么分歧。但由于历史环境、时代性格和个人经历对于诗人的主观性的教育作用,他们进而要求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必须通过严格的自我审察,争取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相通——即使是个人色彩最浓的爱情诗,也必须象阳光下面的一滴水珠,反射出时代和人民的精神光泽——,而不能象在抗战以前的书斋、讲坛中一样,让诗成为与世隔绝的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的独自。前面说过,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对于四十年代的这一批文学青年,诗不可能是自我表现,不可能是唯美的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娱乐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诗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诗就是激励、鞭策自己的入党志愿书。试用理论文字来说明,他们坚定地相信,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依靠时代的真实,加上诗人自己对于时代真实的立场和态度的真实,才能产生艺术的真实。脱离了前者,即脱离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血肉内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血肉内容,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的;同样,脱离了后者,即脱离了诗人为人民斗争献身的忠诚态度、把人民大众的解放愿望当作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忠诚态度,也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的;而且,如果不把两者结合起来,没有达到主客观的高度一致,包括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同样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要研究这个流派——一般称之为“七月派”——在文学生上的特色,这种创作态度应当说是他们的最基本的特色之一。文学史家们如能对当时整个创作情况掌握比较全面的资料,当不难理解“七月派”诗人们所坚持的这种创作态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当然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完全做到了他们希望做到的。人是复杂的社会个体,他们有时也会在不健康情绪的支配下,写出一些脱离人民的消极的作品;但他们能够觉悟到,这类作品不论是谁写的,即使是自己写的,也决不是严酷的壮烈的四十年代所应有的。事实上,尽管他们主观上要求在自己的艺术中体现人民大众的解放愿望,但限于生活环境和工作岗位,他们当时大都还难于甚或不可能同工农群众有更直接、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加上一般说年纪都比较轻,因此对生活内容的理解和对艺术方法的掌握也都还不够成熟。这些主客观的限制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上,便是题材较狭隘,宵词较迂远,感情的知识分子气息也较浓。综观这本诗集,作者们早期的作品写在爱国主义热情尚未衰退的年代,创作的情操比较单纯,生活的旋律比较欢快,作品的色彩也比较明朗,那些历史的限制还不太显著,后期的作品则是更其复杂的历史环境的产物,作者们不但继续面临民族的大敌,而且在生活周围的各个角落,都遭遇到空前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黑暗势力,人和诗在原来的生活环境下便日益感到那些历史的限制,作品的情调也不得不日见沉郁和悲怆起来。对于那些主客观限制,诗人们并非没有自觉,正是为了突破那些限制,求得和先进人民的结合,他们不少人都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纷纷进入了解放区。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和进展,他们更多人告别了过去,甚至告别了自己心爱的诗,和全国人民一起,准备迎接伟大的祖国的新纪元了。
以上就是本集作者们作为一个流派的起源、性格和特色,以及他们对于人和诗的关系的一些理解。他们在有限的创作历程中所积累的一点甘苦,究竟正确与否,不必也不可能按照抽象的普遍的理论根据来评断,它更需要由实践来检验,不仅要由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检验,还应当由其它流派以及后来者的创作实践来检验。一种艺术见解的正确与否,提倡者本人未必会有充分的实践和成就来证明,反倒更能由不同流派的同代人和后来者,经过批判性的实践加以肯定和提高,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对于中外文学遗产,本集作者们从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尊重古今一切有成就、有贡献的诗人,但他们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他们认为,只有在自己所走的路上有所前进,即在争取与人民相结合的生活过程中,能用自己经过锻炼的情绪、想象、意境以及形象思维的凝聚力,帮助扩大了诗的独创性的领域,才是对那些可敬的同行们和先行者们最谦虚、最诚恳、最忠实的态度。趁本集问世之便,把作者们的几点共同理解写出来,没有其它任何用意,只不过为他们在四十年代的一段努力作一点诠释而已。
说到四十年代,已经有人指出,在某些新文学史家眼中,它仿佛不过是一片空白。其所以这样看的理由和原因,这里无庸详究;但历史本身将会证明,这个看法是不公允的,也不正确的。德国的浪漫派欢喜把历史学家称作“向后看的预宫家”。如果中国的新文学史家并不驰心旁骛,也可算这类预言家之一,他至少应当根据精神世界的“周期律”,预言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之间,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未知的元素”,从而鼓励人们去探讨。事实上,在新文学史中,四十年代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应当说是一块巨大的里程碑。单就新诗而论,随着抗战对于人民精神的涤荡和振奋,四十年代也应当说是它的一个成熟期。如前所说,不但诗人艾青的创作以其夺目的光彩为中国新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更有一大批青年诗人在他的影响下,共同把自由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无法企及的。本集作者们一致认为,这个“高峰”的意义应当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自由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经过四十年代的优秀诗人们的努力,已经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发展基础。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自由诗作者们在形式上所表现的弹性和动力,在词句上所散发的新鲜气息和感情色泽,在形象上所反映的个人独创性和社会内涵的一致,无不说明自由诗不需要任何假借和依傍,可以而且应当直接来源于生活。从这个意义来说,自由诗力图恢复诗的本色,正是一种在文学创作上追本溯源的劳动,同时也是一种克服以“流”为“源”的异化现象的斗争。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优秀的自由诗是同民族的、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衬切相连的,它的发展过程也必然是同当时诗歌领域里一些固有的封建性思想感情、以及一些外来的现代派的颓废思想感情相排斥、相斗争的过程。如果说诗是历史的回声,四十年代的自由诗运动正是从这两方面完成了它的庄严的任务,从而使诗作为人民的心声达到了真诚而纯洁的境界。本集这二十位作者也正是在这个四十年代,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接着发生的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为自由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超过了一点促进作用.他们从事自由诗创作的这一段努力,虽然难免种种可指摘的缺点,不也隐约地反映出整个四十年代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风貌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相信公正的历史也不会永久忘记他们的。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批诗人一齐被迫搁笔了,有的接着相继谢世(如阿垅、方然、芦甸、郑思、化铁等)。他们今天能够重新与读者见面,正显示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恢复。但,文艺写作毕竟只是一种个体精神劳动,这些诗人的已有成就既然各不相同,他们今后的发展也都难以逆料;他们作为一个流派而存在,只是指历史上的情况而言,这本诗集主要地记录了他们当年所走过的一段道路。他们有些人或者已不再能写诗,或者一直坚持写作,但在进行新的探索,他们所走过的这条道路却并没有封闭,永远会有后起之秀在继续前进,并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无疑是使他们感到欣慰的。
由于资料散佚,搜求困难,本集所选未必是各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更不足以概观某些多产诗人的全部创作成果。加之篇幅有限,编辑人只就力所能及,向读者展示一下他们风姿的一片投影而已。要对其中一些重要作者进行全面评价,还有待于他们各自的专集问世。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自诗人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本文首发论文邦:http://www.lunwenbang.com
上一篇:犁过大街,犁过城市的心脏
下一篇:参加会议的有北京、成都、重庆的诗作者及评论工作者共三十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