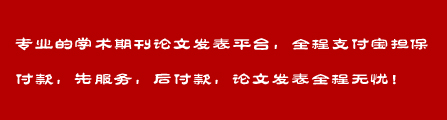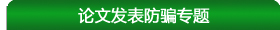由于许多学者意识到诗的本质与言说方式有关
日期:2010年06月29日 来源:原创 热度:
由于许多学者意识到诗的本质与言说方式有关,即跟形式、结构和语言型态有关,现代汉诗的话语形式问题自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光明认为文类成熟的标志是基本规则的形成,但似乎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说:新诗的主要体式是自由诗,是诗体解放的产物,这往好处说,是每一..
教育论文发表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论文发表网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
由于许多学者意识到诗的本质与言说方式有关,即跟形式、结构和语言型态有关,现代汉诗的话语形式问题自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光明认为文类成熟的标志是基本规则的形成,但似乎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说:“‘新诗’的主要体式是‘自由诗’,是‘诗体解放的产物’,这往好处说,是每一种独特的经验只能用独特的形式来凝聚;往坏处看,则是写诗种种误会的根源。从‘押韵就好’变成‘分行便行’决不是诗的正路。诗的成熟最终都在诗歌的某种话语形式上得到体现。”但是现代汉诗应当拥有怎样的“话语形式”?他只是提出“创造最切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让它成为创造者与欣赏者共同的桥梁。”研究显然还有待展开。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抒情话语与抒情诗》将抒情话语分为简单、复杂两类,引入类型的规约形式所隐含的“说者、听者、参与者之间的交织和回声”对文类的震荡、瓦解和重组,考察了个人激情与“大我”相遇,然后形成“政治抒情诗”这一文类的过程。但他过分重视抒情话语情绪与身体的关系,关心的是话语的生理关联和意识形态内涵,对文类话语特征和形式因素并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倒是王珂(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拓展内容职能,定型诗形诗体》的论文中表达了汉诗文体的构建理想,以承认写作的级次存在为前提,提出了“有限地规范多级性多载体的诗歌”的主张:在突出诗的精炼美、音乐美和排列美的原则下,“增加汉诗的艺术门类,并界定出各个门类相对的文体特征”。这似乎是对世纪初新诗运动中提出的“增多诗体”主张的呼应。“五四”以来人们似乎更关心用新工具“运输”新思想新精神,后来定出一个第一第二的标准,诗歌话语形式的问题实在探讨得太少。
然而没有一套形式规范来使自己定型,便无法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格局中为自己定位,这是骆寒超论文《新诗的规范与我们的探求》里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走律化之路的”,在现有的诗体中,他最赞赏的是引进西方十四行诗形式用以表达中国经验的实践,以为新诗的话语形式也可以通过借用洋诗体进行转化,朱湘、李唯健、冯至、唐祈、郑敏等都写出过优秀的十四行诗作品,他们将本土经验、现代汉语特征与十四行形式交融汇通的成功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与发展。
沈奇的论文《拓殖、收摄与在路上》也提出“由放任的拓殖到自律的收摄,是成熟起来的表现。……仅凭精神驱动造就的只是大批热爱写诗的人,以及几个‘登高一呼’式的‘风云人物’。只有那些潜沉于诗歌艺术,且具有整合能力的诗人,才会成为真正优秀的、跨时代的诗人。”但他认为“收摄”是指在精神拓殖中,找到更契合的言说方式,即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诗歌艺术,却不主张形式上的“锁定”。他认为“规定什么是诗,肯定是错误的思路,但指认什么不是诗,是否是当代诗学应该考虑的问题?”他觉得在绝对原则与绝对自由两极之间, “该有个可通约的过渡带”。白灵(台湾《诗学季刊》)则主张在“外规”(公认的诗的游戏规则)既无、内规(自定的诗的游戏规则)亦乱的情况下,应当“对诗语与诗意的浓淡、清浊、长短做适度的裁剪和制约”。他在论文《诗的浓度、浊度与长度》中,大胆引入化学各词,通过“溶剂”与“溶质”的对比关系,分析了神话性语言(诗化语言)与逻辑性语言(解析性语言)的特点及其在诗歌中的意义,认为“综合互溶此二者,使其浓淡适当、调配得宜,当是诗人可注意之处”。而萧萧(台湾诗人)则在论文《台湾散文诗美学》中,通过台湾40多年的散文诗作品,探讨了散文诗这一文类的特点。他是把散文诗作为诗的一种体式来看待的,“是用散文的语言完成诗的瞬间”,“通过戏剧般悚栗效应”表达现代人的生存经验。当然,散文诗是诗之一体还是独立的文类,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看法,旧有文类通过艺术家的“打通”与组构,判定它是“次文类”还是新文类,往往要看它的陈述结构或建架。
在现代汉诗型态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进入到诗歌话语、形式与表现策略等具体层面的探讨,但话题还比较分散,范畴与概念还不大一致。人们只是开始意识到,现代汉诗的成熟型态,是创作规则及手段稳定下来后构成的体系,必须同时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在目前写作目的过于明确而语言型态又不很稳定的状态中,提倡形式与规则的探索,意在强调对现代汉语特性的认识和反思,以便更自觉地根据这种语言特性寻求诗形并在丰富汉语的美和表现力的向度上追寻。
本次研讨会另一个热切话题是90年代的中国诗歌写作。谢冕的论文是《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他认为80年代充满热情的试验与创造,促成了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格局,90年代“中国诗人所拥有的创作自由可说是空前的,诗歌这匹过去受意识形态严重羁束的马,如今挣脱了缰绳而一径狂奔起来”,它使诗的出发点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中国诗中的‘豪情壮志’,……那些高高在上的众口一词的宣讲结束了,弥漫于诗行中的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普通与平凡。”他认为其中较有价值的是那些虽是讲述个人性经历、却使人联想到更多的人经历的作品,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诗歌。(“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歌成就中,除去‘朦胧诗’在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方面的贡献是别的成就无可代替之外,唯一可与之相比的艺术成就,则是女性诗歌创作。”)然而,在诗的个人化的倾向中,大量的诗也表现了对历史的隔膜和对现世的疏离,“在标举诗与‘代言’无关而倡导‘纯粹’的背后,无需否认,其间有着刻意的回避与隐匿。”
与谢冕肯定诗歌回到“个人”后题材、表现的“丰富”却不满精神与理想的“贫乏”相近,徐敬亚(深圳)在论文《隐匿者之光》中把90年代的个人写作称作“散漫期”,“我看不见它在哪里。没有显著的事件给我以标明,没有足量的作品让我兴奋……80年代中期现代诗大试验的洪峰依然在缓缓退却,男敢而鲁莽的探索者们留下了贝壳狼借的沙滩。中国的诗歌大军在追赶西方大师的中途,忽然一哄而散。”他认为诗坛“被资本那油腻的手搅得一团和气。严厉的地平线已一团模糊”。诗人陷入了无物之阵。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则从“读不懂”的角度表示了对90年代的不满。他幽默地说:“朦胧诗出现时,我反驳过说读不懂的人,如今轮到我读不懂诗了。”他在《后新潮诗的反思》的论文中认为“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显然也有新探索,但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突出,……现在流行的却是,写诗首先要远离自己,远离中国人的感觉和心灵的底蕴。”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论文《从“崛起诗”看中国新诗的前途》不谋而合地呼应了这种观点。他把“文革”后的诗歌分为“崛起”(“朦胧诗”)、“继起”(受“朦胧诗”影响将意象化推至极端的诗潮)、“后起”(叛逆“朦胧诗”的诗潮,或被称为“新生代”)三次诗潮,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新诗的前途只能从‘崛起’诗人的探索成果中去寻证,这些成果包括社会人生批判的深刻性和生命体验的个性化,包括在丰富性前提下诗歌题旨的意义要素备受尊重,包括意象表现的合法性及它的合理密度的安排,更包括诗歌内部意象联结的多样性及鲜明的逻辑关系。”他觉得“继起”诗人的意象泛滥和“后起”诗人疏远意象,是走了疏远读者与投合流俗两种极端。
一部分学者认为90年代诗歌存在着另一种观看、命名的可能性。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试图“告别”与自己熟悉的知识系统,“适应”并以另一种知识系统来把握90年代纷繁复杂诗歌现象。他认为二元对立式写作时代已经逝去,个人写作和相对写作时代已经到来。“诗是社会生活的承载者”到“诗就是诗”的诗学观念的变移,首先确定的是诗对种族记忆的保存,诗人的职责不单是民族的良心,而主要是在这一工作中的对语言潜能的挖橱,“他是为语言的最理想的存在而写作。”柯雷(Maghiel Van Crcvel,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亚洲学院中文系)不把90年代诗歌作为一个需要与80年代诗歌严格区分的范畴,而将其看作是“三十年前的最早开始以来迅速而多元的发展”的“实验诗歌”。在论文《实验的范围:海子、于坚的诗及其它》中,他认为“实验诗歌关键特点之一是它跟政治抒情诗不一样”。他建议把80年代中期出现延伸到90年代的、与朦胧诗截然不同的“生活流诗歌”或“口语诗”称为“反神话诗歌或拆解的诗歌”。他觉得实验诗歌中丰富而有时惊人的意象需要一种“主动而机敏的阅读”。柯雷认为实验诗歌中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为:“语言是一个传达在语言以外独立存在的‘内容’的媒体吗?语言是工具还是目的?是语言跟随诗还是诗跟随语言?语言是描写、模仿现实还是确定、创造现实?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是怀疑语言的能力的一个手段?”
从语言与现实相互关涉、矛盾、规约、反抗的复杂关系中解读90年代诗歌,唐晓渡(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的论文《谁是翟永明?》以具体的诗人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虽然作为一位女性和一个诗人。都使用了“翟永明”这个相同的符号,然而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意义:一方面,作者“不时从作品中消失”;另一方面,“主体并没有、也不会‘永远消失’在写作所创造的空间里”。那么,对诗而言,最值得注意的便是经验、想象的文本转换,——唐晓渡在“生命一语言”的临界点上,阐述了“舞者与舞蹈”的关系,从而确立了诗歌本体的意义。当然不仅于此,这篇文章还带出了女性诗歌的敏感话题。荒林(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认为唐晓渡论文对“女性诗歌”定义质疑,体现出“自我反思”和“话语颠覆”两重意味,反思引入沉思,而强调“文本”的威权却隐含着男性话语的政治观点,企图用貌似客观的“文本”否定女性文学自由、开放的写作策略。她在论文《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中还提出:女性所认为的“现代性”,“不同于那种‘线形时间’敞开的现代性,也不是与此对应的审美现代性‘对大写艺术原则的坚持’,而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历史空间中女性话语主体就此作出的言说,一方面敞向‘时代’(当它‘属于女性’时),另方面背向时代(当它‘非属女性’时)。”林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也在《自觉·自虐·自审》的论文中联系中日女性诗歌的历史发展,讨论了女性诗歌的“三度嬗变”。诗人翟永明(成都)却欣赏“少谈些性别,多淡些诗”的说法。在《面对词语本身》的发言中,她说:90年代以来“我对词语本身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面对90年代诗歌不同的评价立场,刘登翰(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认为当年的链条已经断裂,应当重视不同经验与观点的对话和沟通。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则提出“诗离我们远去”还是“我们离诗远去”的问题,主张面对陌生,采取慎重、深入的分析态度,读者与研究者也需要深入的自我反省。而诗人王小妮(深圳)则通过一则卡夫卡式的寓言,在《木匠致铁匠》中提出了“这世上只有好诗,而没有诗人”的观点,她认为“只要认认真真地在想写的时候,写好每一句诗就已经足够”。而立足眼前从工业革命到电脑革命对人的生活方式和诗的表现方式的影响,杜国清(美国加州大学)提出了“网路涛学”的设想。他在《网路诗学:二十一世纪汉诗展望》的论文中,从创作、构思、想象、意象、象征等方面探讨了网路诗学一些特殊性格和诗的效用。他认为这是新的创作和出版同时完成的超时空写作方式。他还提出:汉字文化的思考方式,并不因科技的发展而落伍,反而与电脑越来越注重图像的表现方式更加接近。因为,“汉诗由汉字的排列组合而成,与电脑网路上的虚拟世界(virtuality)以映象不断变幻的表现在结构原理上并无二致。”这种充满激情的观点可能简化了后工业社会许多复杂的问题,但电脑时代对人的生活和想象方式的改变,以及对诗歌写作的正负面影响,的确值得深思。
除上述话题比较集中的论文外,尚有一些论文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如金龙云(韩国东亚大学)的《七月派诗歌的矛盾结构》、崔建军(江苏盐城社科院)的《冯至诗歌与本体建构》。他们都对自己的论述范畴出了新的见解。此外,一些因临时有事未克出席的学者也向会议寄来了论文,他们是:是永骏(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的(《TheGrowing Accept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Japan》;杨小滨(美国耶鲁大学)的《异域诗话》;罗门(台湾)的《漫谈中国诗与西方现代视觉艺术的关联性》;李怡(西南师范大学)的(论穆旦与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性》。
会议的成功是主办、联办单位愉快合作的结果,更应感谢与会各国、各地学者的大力支持。从筹备开始,福建师范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李建平教授就给予具体关照,并在会议召开与他北京会议相距只有一天的情况下,仍从福州赶到武夷山出席开幕式。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则认真听取了每一位学者的发言,他的题为《现代汉诗的回顾与展望》的闭幕辞,全面总结了现代汉诗的历史行程和本次研讨会的成果。此外,会议还得到武夷山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共南平市委常委、武夷山市委书记陈祥龙先生、副市长衷梅英女士出席了开幕式,市长张建光先生主持了他们欢迎与会学者的宴会,特此借论文集出版的机会,表示衷心感谢。
1997年11月20日,于福州。
本文首发论文邦:http://www.lunwenbang.com
上一篇:、《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办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7月26日至30日在武夷山隆重召开
下一篇:说准八十年代式的诗学趣味